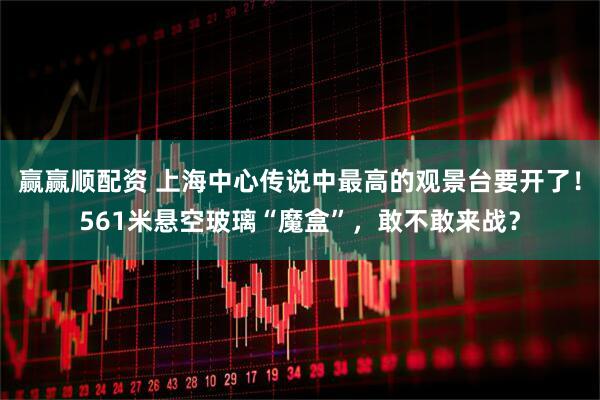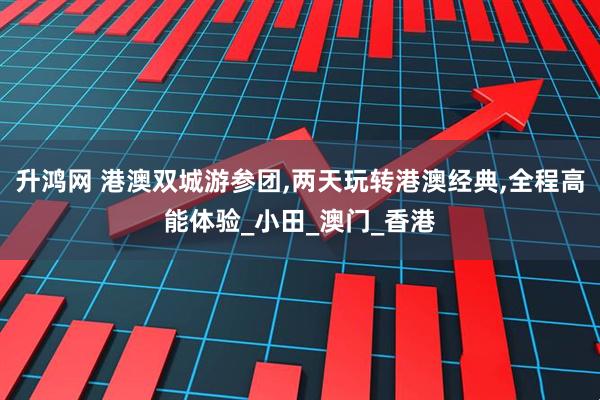《资治通鉴 唐纪四十》记载: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、安庆绪、史思明及史朝义四人父子立祠易资配,尊称为“四圣”,并请求出任宰相。唐代宗派遣内侍孙知古前往劝说,最终促使田承嗣拆毁祠堂。冬季十月甲辰日,朝廷加封田承嗣为同平章事,以表彰其功绩。
公元773年,田承嗣身为魏博节度使,特地为曾叛乱的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四人建祠堂,称他们为“四圣”,更大胆请求担任宰相。唐代宗得知此事后,派遣内侍孙知古前去劝说,最终促使田承嗣拆毁祠堂,并加封其同平章事以示嘉奖。
此时,安禄山遇害已有17年,安庆绪被杀也过去14年,史思明之死12年,史朝义自尽10年,安史之乱已平息整整十年。这件事情看起来极为荒谬:一个叛将归顺后竟为叛乱领袖修建祠堂,朝廷不但默许,还亲自派人劝阻,最后封官奖赏以促使拆毁。那么,田承嗣究竟是何方神圣?
田承嗣是河北秦皇岛卢龙县人,家族世代为卢龙军裨校,隶属于幽州卢龙节度使管辖。安禄山则掌控范阳、平卢、河北三镇节度使,属其上级。田氏家族为传统军人世家,父子相继守卫边疆。
展开剩余80%田承嗣因镇守边境对抗外族屡建战功,官至武卫将军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他随安禄山在范阳起兵,南下攻取洛阳,安禄山令其驻守颍川(今河南禹州)。田承嗣进攻南阳,攻破太守鲁炅防线,鲁炅逃至襄阳,田继续攻打襄阳却未能攻克。
757年9月,唐军收复长安易资配,10月夺回洛阳,安庆绪率叛军退守河北。田承嗣驻守颍川后方被唐军截断,遂率军投降唐朝。后又叛变,追随安庆绪,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,田承嗣转而归顺史思明。
759年,史思明攻占洛阳,田承嗣随军作战,后任魏州刺史。760年,田承嗣率兵劫掠淮西。761年,史朝义杀死史思明,田承嗣随史朝义守河北任丘。随后,田承嗣率军4万迎战唐军仆固玚,遭遇惨败。史朝义亦败退。随后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怀仙、薛嵩等陆续投降唐军,史朝义孤立无援自缢身亡,首级被李怀仙献给唐军。田承嗣则将史朝义家眷送入仆固玚营中。
田承嗣是安禄山与史思明旧部,屡次背叛朝廷,为求自保甚至出卖史朝义。为何他会为安禄山、安庆绪、史思明、史朝义父子建立祠堂,尊为“四圣”呢?
首先,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有人说他们在河北人心所向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安史叛军内部忠诚度极低,将领频繁投降反复无常,且叛军在河北多次屠城掠地,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,民间绝无所谓“圣人”之说。
实际上,建立祠堂、尊四人为四圣的是田承嗣及其安史旧部,非河北民众所为。安史叛军旧部在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怀仙、薛嵩等叛将统领下投降唐朝,几乎整支军队得以保留,很多将士曾随安禄山、史思明作战。
《新唐书·张弘靖传》记载:河朔旧将与士卒习惯于称呼安禄山、史思明为“二圣”,唐穆宗长庆年间(821—824年),张弘靖任卢龙节度使,为扭转这种风气,掘开安禄山墓穴毁棺,引发士卒不满。可见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影响力深植军中,传承数代,但在河北百姓间并无此说。
安禄山、史思明在军中影响力主要源于以下几点:其一,安禄山曾提拔众多将领,田承嗣便是从卢龙军裨校一步步晋升,借助安史之乱实现阶层跃升,怀有感激之情。其二,安史叛军数十万兵马及家属皆依赖安禄山、史思明供养,军队人员自然尊敬他们,视其为“圣人”。其三,安禄山、史思明积极塑造自身形象,军队纪律严明,适合树立领袖权威,时间一长,其形象深入人心。田承嗣建立祠堂,或借助其生前的宣传形象。
其次,田承嗣有明显私心。归顺唐朝后,他暗中招募亲兵,组建约一万人的衙兵队伍,形同私军,既不尽忠朝廷,也未履行臣子职责。
田承嗣以魏博节度使身份掌控地方,实则意图将职位私有化,借助安禄山、史思明影响力巩固自身军权,拉拢旧部,试探朝廷容忍度和军事实力,谋求割据河北。这种种举措皆为其私利考虑。
第三,宗教因素也发挥作用。安禄山是粟特胡人,史思明可能是突厥或粟特人。安史叛乱最高领导多为胡族,旗下将领也有沙陀、契丹、突厥、奚族、鲜卑等多族裔,形成多民族军队。
安禄山手下有曳落河、同罗精骑等胡人部队,管理胡族须借助宗教影响力。据荣新江教授研究,安禄山利用本族宗教袄教(拜火教)巩固统治,在范阳举行宗教祭祀,增强军心。
袄教源自中亚波斯及粟特人,信徒多为胡族,且对铁勒、稽胡等突厥语系民族有较大影响。袄教北魏时传入中国,华夏人中信仰者少,但胡人中极盛。安禄山利用宗教巩固对胡人部队的控制,这种影响力自然而然延续至河北旧军。
田承嗣麾下也有大量胡人,为了拉拢这部分军力,他便效仿安禄山为四圣建祠,借此巩固兵心,争取军队支持。
综上,田承嗣为“四圣”立祠,既有利用安禄山、史思明影响力以稳固军权的政治目的,也包含宗教上的考量,更是其私心的体现。
发布于:天津市海通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